中國有馬云難有喬布斯
馬云成功還有一個值得稱道的重要因素是他的刻苦學習,學以致用。人說馬云的真經是:西方治理,東方智慧。馬云說:“我從道家悟出了領導力,從儒家明白了什么叫管理,從佛家學到了人怎么回到平凡。這些思想融會貫通,剛柔相濟,就是太極。”他翻閱到《老子》第九章:“功成名遂身退,天之道。”馬云功成名就,《華爾街日報》2011年舉薦他是喬布斯的繼任人選之一,也有說,如果馬云能再在公益、環保、創業教育等領域有所建樹,他將有可能最終進入洛克菲勒、福特、蓋茨、喬布斯等世界級企業家的行列。
本文引用地址:http://www.j9360.com/article/153124.htm那么,中國有沒有喬布斯呢? 馬云說:“美國的偉大在于創造出一批這樣的人物——馬克扎克伯格(Facebook創始人,人稱蓋茨第二)、喬布斯、貝索斯(全球最大的互聯網書店——亞馬遜網絡購物中心締造者)等一群人。中國只有一個或兩個,如何能產生出一群類似的人物,這是中國應該思考的問題。”是不是可以這樣認為,馬云的回答是中國有喬布斯的,如上所述,本就有人稱馬云為喬布斯。國人曾經排隊搶購《喬布斯傳》,其意當在許多人都想探求喬布斯的成功之道,而后成為“中國的喬布斯”!中國媒體如《參考消息》也在頭版頭條載文《中國呼喚喬布斯式的創新人才》。而李開復則在微博上說中國出不了喬布斯,他認為不是中國人不夠聰明,而在于教育太注重背誦和記憶,不鼓勵批判性思維。這無疑是理由之一,筆者認同這一看法,中國還沒有產生喬布斯的土壤,理由如下: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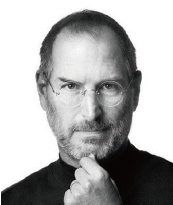
商業為上 中國早在商朝便出現商業,商民善于經商, “商邑翼翼,四方之極”(翼翼,眾多也;極,頂點),故后世將經商的人稱為“商人”。簡略數數中國歷史上的巨商大賈即有富甲陶朱--范蠡、 儒商鼻祖——端木子貢、智慧商祖——白圭、營國巨商——呂不韋、富可敵國——沈萬三、商業巨族——喬致庸、紅頂商人——胡雪巖等等。我國歷代統治者大多尊士抑商,“士農工商”是傳統社會的定位序列,實際并沒有擋住“商”的興隆發達,公元前二世紀,史家司馬遷就指出了當時財富積累特征是:“農不如工,工不如商”。北宋時期商業更達到了一個新的轉折點,它去除了商業活動在時間和空間上的限制,同時,政府允許工商業者“以資買官”,商人地位有所提高,形成了地主、官僚、商人逐步結合的趨勢,財富來源與授權經營壟斷產業有關,如此官商經濟模式產生了深遠的影響。2013年《財富》世界500強中,中國企業增至89家,10年來連續獲得增長值得慶賀。但觀察入圍的89家企業中,民營企業僅7家,最突出的問題是“過度金融化”,9家上榜銀行,而其利潤占到中國上榜公司利潤總額的55.2%,超過一半還多。金融業屬第三產業,利潤來自實體經濟,而今攫取利潤過多,勢必大大挫傷實體經濟的生產積極性,導致經濟空心化,或釀成經濟金融風險,令人心憂。同時也反映了今天依然是“工不如商”,馬云經營的阿里巴巴集團屬商業領域,他可與馬克扎克伯格、貝索斯為伍,與喬布斯可并不搭界。
工業后進 在人類社會經濟歷史發展長河中的農業社會時期,直到明朝中國長期走在世界經濟前列,占有世界經濟中心的地位。1769年,以英國為首開始工業革命,世界邁向工業社會,正值清期“康乾盛世”的乾隆年間,中國還自以為“天朝大國”萬國來朝的盛世之邦,實施閉關鎖國之策,從此經濟走向衰落,不斷受到列強欺凌,中國雖有“洋務運動”的興起,仍不免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。1945年世界掀起第三次革命――信息革命,向著信息社會前進,我國也曾屢次提出“四個現代化”建設,而中國至今仍處于“工業化中期階段”,實施工業化與信息化的融合,體現了中國工業化道路和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。中國信息化建設雖已取得了一定成果,但仍沒有實現與工業化的融合,制約著工業化的推進。電子信息技術是現代技術進步的主流,我們應大力發展信息技術和相關新興產業,以便趕上世界經濟發展的步伐。喬布斯產生于信息化發達成熟的世界第一經濟強國――美國,并非偶然。美國是電子信息工業發展的源頭,許多電子產品諸如音像產品、雷達、大型計算機、PC、液晶電視全都發明于美國,正當PC、液晶電視市場走向成熟,電子產品發展前途茫茫然之際,正是喬布斯推出了一系列“i”產品系列,從大寫的“I”變為小寫的“i”,電子產品更加小巧玲瓏,美觀實用,便于攜帶,創造出新的需求,改善了人們的工作和生活,導致“人人變為低頭族”!世界進入移動時代,移動互聯網應時而起,中國市場很大,產品則大多是“Copy to China”,自然難有喬布斯。
創業維艱 蓋茨、喬布斯都是大學沒讀畢業,中途輟學從業的世界級科技精英,他們創業有“風險投資”的支持,他們開發的產品有應用的社會環境。《北京青年報》日前報道,我國“今年大學畢業生創業人數僅1%”,原因是“貸款不夠‘貼心’,政策不接地氣”,貸款困難,政策支持力度不足,并建議“大學生創業宜從服務業起步”,如此大學生所學技術何用? 更何來喬布斯乎?
知識欠尊 《管子•小匡》說:“士農工商四民者,國之石(柱)民也。”上面講過,原先士農工商的排序并沒有擋住“商”的發達高遷。士泛指“士”(讀書人)和“仕”(當官者),“學得文武藝,貨于帝王家。”當了官的“仕”當置首位,出則輿馬,入坐高堂,一呼百諾,金玉滿屋,名利雙收,萬眾側目,足證“萬般皆下品,唯有讀書高。”士(讀書人)則不盡然了,只能說一般較好,古語有云:“百無一用是書生”,知識無用;“千古腐儒騎瘦馬”,命薄福淺。可見知識無用,士人命薄是古來自有的。我國上世紀五、六十年代曾流行過這么一說:知識分子從小學讀到大學,只有書本知識,肩不能擔手不能提,殺豬豬跑,五谷不分,“其實是比較地最無知識的”,年長如我者對此說無不刻骨銘心,自慚形穢。改革開放以來,黨對知識分子問題的認識不斷深化升華,強調知識分子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重要力量,形成了尊重勞動、尊重知識、尊重人才、尊重創造的基本方針政策。當今世界,科技發展突飛猛進,創新創造日新月異,知識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的作用日益突出,隨之也頒發了《關于發揮知識分子作用改善知識分子工作和生活條件的規定》等。政策很好,可落實常遇阻走樣,正如近在大眾媒體上讀到的一句話說:“理想是豐滿的,現實是骨感的,”至今知識分子還是千軍萬馬爭考公務員,原因很簡單,無非公務員有權有利,高人一等,不愿去坐冷板凳從事科研工作,而科研恰恰又是推動今天經濟發展社會進步的原動力。再者,官大學問大,一當官便成專家,Power is knowledge;知識分子是民族的大腦,直待翻身換時,Knowledge is power,摒棄自古以來的官本位思想,喬布斯就有可能在中國出現了!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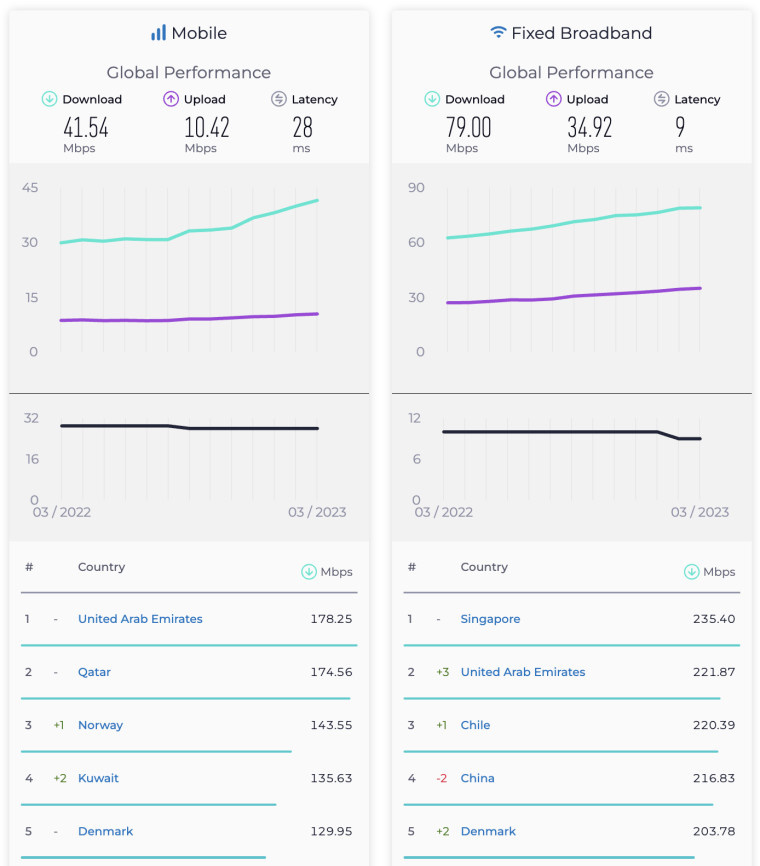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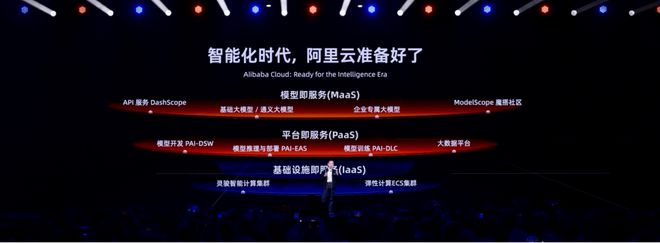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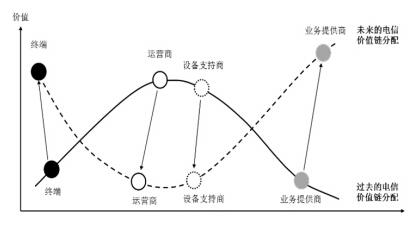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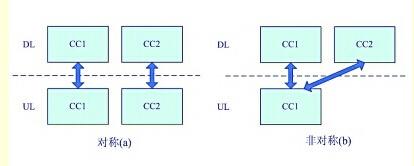

評論